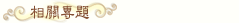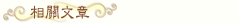《三堂会审》用三审一答的问案场景形成独特结构,突显戏曲浓缩、精华的演出型态。叙事最忌流水账,传统戏曲善用巧妙,营造出发人深省的主题,从头到尾间不容发,让人看的目不转睛,溶于琴弦与锣鼓之中。《三堂会审》又名《玉堂春》,是善良蒙冤的一首“命运交响曲”,苏三遭人诬陷,已被贪官问成死罪。昔日恋人王金龙出任巡按,急于平反,但官场有其步骤,不容造次,他需谨慎从事。
苏三用倒叙的形式交待案情。三位审理者:一是当事人(王金龙)、一是批评者(蓝袍刘秉义)、一是同情者(红袍潘必正),用三种不同的观点观看此案情。舞台表现手法高明,即使比之今日电影最时髦的多观点叙述技巧,也毫不逊色。
藉这四位演员的做表、神情,引领观众进入过往情境;观众本身也成了审理者,参与在抽丝剥茧的问案中。然而近代的编剧者,不能理解此剧的奥妙手法,嫌《三堂会审》没头没尾,竟将苏三所倒叙的事情,增编演在前面(为的是告诉观众苏三讲的是真的,如此却让审案丧失悬念的趣味);最后又加演王金龙与苏三结婚团圆(古人的智慧早就有“开放式”结局的编剧法,观众自可联想,实不必一一道尽)。这其实是不尊重古人,自以为是的“改良”京剧,却不折不扣改成流水账的结构,让人看的累赘与乏味。不但不能使原剧加分,反将原来的精彩,变成黯然失色。
开场是都察院三位官员会审的大场面,苏三战战兢兢的上场,跪在堂下。王金龙高高在上,乍然见到已嫁作他人妇如今身陷囹圄的旧情人,立即气血翻涌,昏厥过去。舞台立即起了大变化:解差带着苏三暗下,潘刘二位也暗自下场;王金龙的“大帐”放下,衙门改成病床(如此俐落的场面调度令人惊奇)。接演“请医”,胡琴演奏“柳青娘”的曲牌,医生随着背药箱的童子出场。老医生戴白“八字”髯、小帽头、便装,手持马鞭,到台口下马,从药箱内取出官服(纱外套)换上。然后请安、进院、就座、把脉。中规中矩又突梯滑稽的“哑剧”,将王金龙的心中“隐情”烘托出来。这是个很短的桥段,却起着平衡的作用,它冲淡了都察院的严肃,让大家轻松以对。有些演出将它省去,这是不理解剧情的转折与层次,“请医”暗喻王金龙是如何着急的想平反这个案子,是不能省去的。
| 《三堂会审》苏三(顾正秋饰演)跪着陈述案情。情深义重的苏三,是顾正秋最喜欢的戏曲人物之一,这是顾正秋早期在台北永乐戏院演出的实况。 |
审案开始,剧情进展的很缓慢,苏三戒慎恐惧的唱着,每唱一句三位审判官就议论一番。王金龙护航心切,但是总被不留情面的蓝袍刘秉义打断;王金龙强忍,以陪笑撑过。苏三跪在台口面对观众(这类似电影的特写。如果按写实剧场的办法,苏三只能背对观众,那就太不知变通了),由西皮倒板、慢板、原板(原板用的最多,是这出戏的主要节奏),进而二六、流水、快板与散板,几乎将西皮所有的板式都唱全了。尤其梅兰芳1935年在百代录制有这些唱段的唱片,因之这出戏传唱的很广。
随着音乐的结束,观众对案情也了解了,同情心油然而生。苏三的为人明白若揭,她虽然出身风尘,但在王金龙落魄时不断伸出援手,她从没被势利的环境掩盖住她本性的善良。这出戏的重点并不在于如何洗脱苏三的冤枉,而是苏三的“爱”让人感动:关王庙她见到沦为乞丐的王金龙,“不顾肮脏怀中抱”。这种对所爱者的不嫌弃,尽管他是个失败者,她照样宽容、接纳他,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
苏三与王金龙分离后,经历恶劣的命运:她被诓卖为妾,又被大太太妒忌,诬陷她谋杀亲夫,收贿的知县将苏三屈打成招,眼看就要丧命,但最后她能堂堂正正的走出魔难。这是她光明的本性,有以致之。命运安排苏三处在吃亏的环境,但她不屈服,她的意志坚定、心境皎洁;所以能被她所关爱的人感应到,为她出面重审冤案。苏三不被障碍限制,她有正念,因而促使了命运的改变,《三堂会审》演示出这个动人的脉络。这出戏进展的很平和,没有什么激烈的抗辩与强求的手段,在音乐的旋律中,自然而然的洗刷了苏三的冤屈,观众也见证了正义的可贵。@*
(//www.dajiyuan.com)